八十歲的山崎豐子仍然著作不輟,以將近五年的時間完成《命運之人》,不僅在質量上能與以前的所有作品匹配,在取材、故事情節和整體的布局都是上乘之作,2012年從一月到三月在TBS電視台上映的十集連續劇,由本木雅弘、松隆子和真木よう子所主演的日劇也相當精彩。
以1971年開始的西山事件為藍本,當時每日新聞的記者西山太吉從外務省得到關於沖繩返還協定之中的密約,洩漏給國會議員,在國會之中質詢總理佐藤榮作,由於事涉國家機密,遭到違反國家公務員法起訴,最終以有罪判決定讞。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佐藤榮作組閣,與美國的尼克森共同發表聲明,美國答應支付長期占用沖繩土地的租金和將軍用設施恢復原狀的費用,然而,在條約中公開載明由美國支付,私底下卻是日本政府自行墊償。日本政府由於民情沸騰,希望美軍退出戰後以來長期占領的沖繩,以得到主權完全的獨立,故在推動外交時,透過密約的方式,以早日換取沖繩軍事基地的返還。
當西山公開政府密約後,有關當局仍然否認密約的存在,透過司法檢察系統的運作,嘗試將輿論的方向導到洩漏國家機密,加上西山的情報來源是已婚的女事務官,致使男女緋聞占據了報紙的版面,檢察系統將起訴的方向定位為兩人之間的私通,使得原本擁有正義形象的記者,成為周刊小報街談巷議的八卦消息,掩飾了原來出賣國家利益的政治人物。
國仇家恨(美軍長期佔領沖繩及其留給當地的問題,日本是否能從美軍佔領下走向正常國家)、新聞媒體的報導自由、政治介入司法、記者與情報來源的不正常關係、介入他人家庭的不倫關係,以及由此而來的親情倫理衝突,構成了山崎豐子《命運之人》豐富的故事經緯。
山崎豐子長篇小說中的人物,經常有著「一念一生持」(《太一金華宗旨》)的感覺,相信一個正確的方向,十分單純的信奉著,有時甚至單純到有點幼稚,《白色巨塔》的里見、《不毛地帶》當中的壹崎正、《華麗一族》之中的萬俵鐵平,執著著自己的信念,有的角色在遇到困難時還會轉彎,換一條路以迂迴的方式達成自己的目標;有的角色則是完全的一路向前衝,落得了悲劇英雄的下場。
《命運之人》的角色設定顯然是後者,為了追求事實真相的記者弓成亮太,單純的相信記者就是將事實呈現給讀者,那些收取別人好處,說別人好話的事他做不出來,會從事記者的原因在於戰爭期間新聞只是政治宣傳,無法將真實的情況傳播給大眾,如果大眾了解事實,就可以改變政治,進而改變未來。他相信媒體必須永遠站在政治的對立面,挖出政治的黑暗面,以實現正義。
弓城亮太的兩個女人,一個是無怨無悔支持他在外面拼事業的妻子由里子,另一個則是將祕密情報交給亮太的外務省事務官三木昭子。一個是正宮,一個不倫的第三者,兩者雖然處於對立面,卻都為了支持所愛的男人而犧牲,三木昭子對於沖繩的返還與否可能沒有太大的興趣,國家、社會那種大世界的事她們不想管,但可以成就所愛的人,極機密的文件也只是為了維持關係的手段,三木昭子帶出一份一份的文件,也只是換取她在婚姻之中所得不到的愛;相較之下,正宮由里子想要的是甚麼呢?年輕的她可能是支持亮太那股略帶傻勁的熱情,之後為了家庭、小孩,最後可能只是帶點不甘心的說:「我不想輸給那個女人!」
命運之人這個略帶宿命的書名,在宿命之中帶者積極的面向,我原本以為山崎豐子對於結局的處理如同《華麗一族》的萬俵鐵平,彷彿希臘悲劇中的所有主角一般,當角色的個性設定了,悲慘的宿命就註定了其自殺的命運。然而,山崎豐子對命運有更樂觀的詮釋,當弓成亮太輸了官司,在九州支持他的父親也去世,想要重振家中的青果販售事業,卻遇上了颱風,命運的厄運一個接著一個,使他拋棄自己,浪跡天涯,然而,冥冥中的力量讓他一路南行,走到了沖繩,望著蔚藍的海,天崖海角一躍而下,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命運自有其安排,萬念俱灰的弓成被一個國中時遭到駐沖繩美軍強暴的少女救起,兩個懷抱著痛苦過去的人,在沖繩重新展開人生,弓成雖然揭露美軍沖繩基地的密約,卻未曾到過沖繩,以往只與政府高層官員來往的政治線記者,在沖繩從零開始,瞭解到「真正」的沖繩:被本島人所遺忘和大戰之中飽受戰爭摧殘的沖繩,真正與美軍基地接觸的是沖繩的居民,祖先留下的土地被美軍徵用、婦女可能遭受到美國大兵的人身侵犯和美軍犯罪無法在沖繩得到司法正義,有如現今的伊拉克。當弓成瞭解到了甚麼是「真實」的沖繩,他似乎瞭解了命運的含意,他的生命的起點、人生奮鬥的意義與記者的價值,與群眾在一起,瞭解人民的需要,書寫底層的故事,從下而上,展現每個生命生存的意涵,才是記者的真實。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2012年4月19日 星期四
Restaurant Les 400 Coups, Montreal

蒙特婁的舊城一向都是觀光客聚集的地方,歷史古蹟佈滿於舊城的石板路上,從戴高樂曾大聲高喊:「自由的魁北克萬歲。」(Vivre le Quebec libre!)的市政廳、聖母院到傑克‧卡帝爾(Pleace Jacques-Cartier)廣場。觀光客可以在這裡上一堂新法蘭西的歷史,了解這一群在北美與其他英裔美洲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然而,觀光客多也意味著此地的餐廳都以觀光客為主,指得是食物烹煮得不怎麼樣,菜單千篇一律,卻要價頗高的餐廳。
但是,在舊城寧靜的角落中也還散布著蒙特婁的美食餐廳,像以前吃過的Chez L’Epicier,法式的感覺之中加入魁北克的特產食材與烹調方式,還有近來開幕的Les 400 Coups,其中的一位廚師以前也在Chez L’epicier工作過,舊城之中的新味道,似乎意味著在傳統之中尚帶著點創新的感覺。兩位合夥的年輕廚師,一個是本科出身的廚師;另外一個則是主修心理學,半路出家的廚師,廚藝與心理學,兩者似乎本來就該結合在一起,成功的廚師不會只關注廚藝而不理解饕客們的心理,在絕妙的搭配之中,帶著點天份與大膽,外加一個侍酒師,使得美食、醇酒與心理,由內而外的得到體貼的照顧。如同在其網頁當中所說:

"After having done '' les 400 coups''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400 tricks) , we finally decided to open our own restaurant. We being: Marc-André Jetté as the executive chef, Patrice Demers as the pastry chef and Marie-Josée Beaudoin as the Sommelière. All three of us form a team passionate about the restaurant, food and wine industry which has led us to dream about opening our own restaurant for several months. After having worked together for the past two years and having done a few tricks of our own, we knew exactly what we wanted for our clientele: a cozy space, a refined and inspired cuisine as well as a stimulating and enriching experience. We therefore want to offer you an appealing restaurant which proposes a seasonal cuisine with a focus on using local ingredients and promoting our local talent."

第一次知道這間餐廳是在加航飛機上的雜誌上enRoute閱讀到的消息,去年被評選為加拿大十大新開的餐廳。四月的第一個星期,放假的中午早餐沒吃就前去報到,天氣還帶點寒意,一進門之後,氣氛隨之改變,整體的空間散發著優雅、簡潔和溫馨的感覺,陽光從外面灑入,幾乎全滿的座席之間,擺滿了酒杯與盤子,賓客之間輕聲的談笑著。在我的右邊,整面牆就是一張巴黎Saint-Germain-des-Prés的街角,坐定之後我們就聊起在巴黎的那個角落所散步過的地方,所吃過的餐廳。或許是因為如此,增加了不少親切感,我面對著店內長長的吧台,整個餐廳雖然充滿了食客,卻沒有擁擠的感覺,開始想著是甚麼樣的餐點可以吸引那麼多的人聚集在此。
中午的三道菜套餐是28元,兩道菜的套餐則是22元加幣,在餐點上來之前,沒有吃早餐的我們先吃著薄脆、溫暖且誘人的Baguette和帶著特別香味的奶油。前菜我點的是豬耳朵配上醃製的蘑菇,柔軟又帶點嚼勁的豬耳朵,和廚師特製的醬汁以去除豬耳朵的腥味;妳的前菜是蟹肉可樂餅,外表的皮金黃酥脆,蟹肉與野菜一同混和,顯得清爽且開胃。
進入主菜,妳點的是大西洋鱈魚,鱈魚的下面乘上滿滿的海軍豆(navy Beans),與青醬搭配,海軍豆雖然粒粒分明,吃起來卻具有軟綿綿如絲的口感,鱈魚的外皮薄脆,裡面的魚肉仍然多汁;我的牛排宛如一道藝術品端上來,整體呈現出繽紛的顏色,透過不同總類的蔬菜使得這幅畫如此誘人,蘿蔔、紅洋蔥、南瓜和洋香菜(Persil),這些菜的香味、汁液與牛肉甜美的肉汁相搭配,使得牛肉吃出一股清香。

甜點更是一絕,由於前兩道菜已經讓我們今天的早午餐太過豐盛,甜點我們選了一道共同分享,以日式陶杯盛裝,白色巧克力混合著優格,上面還以淺藍色的小花點綴,帶出春天的感覺,也美好的為這一餐劃下句點。
2012年4月14日 星期六
Natalie Choquette and John Roney

歌劇與爵士樂融合的一晚,即使不懂任何的爵士或是歌劇也沒有關係,演奏者與演唱者都用最輕鬆且專業的方式引導聽眾進入兩者的世界。
必須承認不懂歌劇的我,為什麼會買票聽那塔利‧夏高(Natalie Choquette)的演唱會,多半是因為即使是歌劇的門外漢如我,也曾聽過她的大名,享譽過際的花腔女高音,除了本身的演唱技巧外,她在舞台上搞怪的裝扮,靈活生動的演出,顛覆歌劇正經半百的形象,也是令人耳熟能詳。身為加拿大外交官的女兒,在成年之前就已經來往於世界各地,東京出生,9歲於義大利接受歌劇的訓練,15歲在莫斯科學習聲樂,能以12國語言溝通。她在全世界的巡迴已經不計其數,地位也無庸置疑,令我好奇的是,她會以怎樣的態度和爵士樂合作。
另一方面,今天的另一個主角是同時會彈奏爵士鋼琴與古典鋼琴的演奏者John Roney,出身加拿大的年輕鋼琴手,目前已經錄製了相當多張的爵士鋼琴和古典鋼琴的專輯。他和娜塔莉一樣,對於不同類型的音樂接受度都相當高,也展現了跨界的高度興趣,和娜塔莉有多次合作的經驗。

一開場, 娜塔莉從歌劇如何表達愛開始,唱了幾句經典的歌劇,熱情、誇張且豐富的表情搭配高亢的嗓音,濃烈的感覺應該就是歌劇的表達方式,接著娜塔莉帶著玩笑的口吻,問了談著鋼琴的John,爵士如何表達愛呢?John撥弄幾下琴鍵,柔和且隨興的展現爵士即興的感覺,娜塔莉問了台下的觀眾:「這樣你們能感受到愛嗎?」一來一往之間,歌劇與爵士樂的對抗,娜塔莉充分的將歌劇對於情感的表達以聲音表現出來,John則是在指縫間流洩出爵士的悲與喜。
對於歌劇,娜塔莉熟悉各式各樣的曲目,能夠稱職的表現出最動人的聲音,但是,她也以一貫嘲諷戲弄的方式,調侃歌劇所表現出的窠臼情節,在演唱的過程中,她說歌劇應該具有女性解放的意識,舉例來說:普契尼筆下的《蝴蝶夫人》,故事是十九世紀中葉一名美國海軍軍官到日本,在長崎與一個十五歲藝妓(蝴蝶)結婚,軍官回國後將秋秋桑遺棄在日本,還另外娶了美國妻子,秋秋桑在有小孩子的情況下苦情的選擇了自殺。娜塔莉邊唱邊說如果是她,應該會找個律師要求贍養費與小孩的撫養權。還說這種無聊的劇碼,竟然還有人花錢買票,正經八百的坐在歌劇院欣賞。

娜塔莉從小就在世界各地旅行,浸淫不同的文化,雖然有著深厚的歌劇與古典音樂的背景,但對於各種文化也相當熱中與喜愛,開放的心胸使她與不同的音樂類型合作,頡採不同音樂的本質,以古典聲樂雜揉現代的音樂,跨界演出,展現其深厚的實力和無比的親切感。娜塔莉使我們對於歌劇的印象改觀,與爵士的合作,從兩個似乎對立的類型,在溝通的過程中,漸漸的發現音樂的共通本質。
散場後,帶著愉悅的心情,我們在聽眾逐漸散去的時候,走上前去與娜塔莉分享今夜的心情,她親切且由衷的與我們打招呼,並且問我們從何而來,當我們回答台灣時,她將我們拉到鋼琴邊,在John的伴奏下,與我們一起唱起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知名女高音一起合唱中文歌,聽她分享她在台灣演唱的經驗,對台灣的感覺,她說台灣是亞洲的義大利人,熱情又奔放,我們雖然不一定同意,但很高興她對台灣友好的印象。
走出表演的場地,三月底的蒙特婁夜間還是接近零度,但我們倆心裡都很溫暖,一個晚上的音樂洗禮,在一個友善的城市,和一個對故鄉有著美好印象的國際知名表演者,與我們近距離的接觸,熱情的分享,除了溫暖,還有點魔幻的感覺。
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宮部美幸(宮部みゆき) 的《火車》

火車の、今日は我が門を 遣り過ぎて、哀れ何処へ、巡りゆくらむ (火車今日過我門,哀憐欲往何處去) --《拾玉集》
2011年WOWOW電視台改拍一九九二年宮部美幸的作品《火車》,從當初我看這部小說到現在也將近十年之久,以影像溫習這部作品,彷彿走入時光隧道,從一部社會派的推裡小說重新理解過往的社會。
宮部美幸的《火車》銷售量超過百萬冊,九○年代無疑是女性推理作家的代表,同時也是當時社會派推理的旗手,在宮部的小說之中,讀過的包含:《模仿犯》、《無止境的殺人》、《魔術的耳語》、《這一夜,誰能安睡》和《理由》,如果要我選一本代表作,我應該會將《火車》放在首選,除了是一本推理小說外,也是一個時代的反應,透過一個案件理解泡沫經濟瓦解的九○年代初期,日本社會的破產,不只是銀行金融的破產、也是信用關係的破產,或說是整個人際網絡之間的破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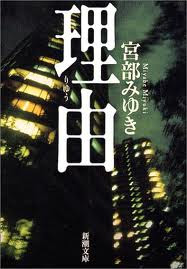
宮部的《火車》之中帶有濃厚的鄉愁,一種對於地方的依賴,生於斯、長於斯所產生的羈絆與情感,所凝聚出的認同,這個地方的關係是相對的穩定且安全。東京對於宮部美幸而言,人際關係的脆弱,來來往往之間毫無認同的感覺,個人脫離了地方之後,在東京之中沒有了羈絆,彷彿在人群中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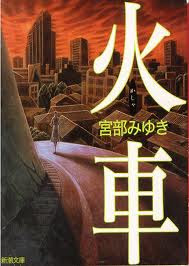
故事的主角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刑警本間俊介,因公受傷在家休養,由於妻子死於車禍,獨立扶養十歲的孩子小智。休養期間,一個遠房的外甥栗坂忽然登門造訪,請求身為刑警的本間尋找失蹤的未婚妻關根彰子,栗坂由於之前幫未婚妻申請信用卡,意外發現未婚妻不為人知的一面,她曾積欠卡債申請破產而導致被銀行列入黑名單,在栗坂知悉這件事之後,未婚妻就不告而別。本間答應了栗坂的請求,在協尋的過程之中,卻察覺事情的背後有更大的隱情。
從當初幫關根彰子打破產官司的律師之處,本間發現了驚人的事實,外甥所認識的美麗動人、楚楚可憐的女子的本名竟然不是關根彰子!那這個自稱關根彰子的女子究竟是誰?真正的關根彰子在哪?是死是活?是假的關根彰子殺害了真的彰子嗎?姓名代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認同,透過名字可以窺見後面的家庭與人際網絡,改名換姓,以另一個人的名字活著,代表著與過去的自己切斷,是甚麼樣的過去,使得假的彰子毫不眷戀地想脫離自己原來的生活?
「迎面駛來的火車--說不定是命運之車。關根彰子要下車,而且她已經下過一次車了。但是現在想要取代她的女性,不知道這情形卻想要叫住火車。她在哪裡?本間對著遠方的黑夜,心中問著:她人在哪裡?還有,她是誰?」

故事中的兩個女主角新城喬子與關根彰子,當她們離開了地方,不管是自願或是被迫離開,缺少了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連結,她們選擇連結的不是一份情感或是心靈的寄託,而是擁有某些東西,一個按照女性雜誌佈置出來的小窩,在東京擁有一個小公寓,擁有自己的空間,從而改變過往的自己,她們相信擁有「東西」是可以使自己得到幸福。
然而,當這些東西,由刺激性消費所生產出來的物品漸漸吞噬了她們的購買能力,在經濟上無法負擔時,信用破產,由物品所構築出的世界崩潰,致使她們所倚賴的認同也跟著垮台。彰子由於經濟上的負債,淪入風塵,致使她再也沒有顏面回去成長的故鄉,失去了地方親戚朋友的支持,形單影隻,最後無法善終。喬子和彰子則是完全顛倒的人生,她是因為父親欠債,從小在高利貸催逼的壓力下長大,致使她脫離故鄉,漂泊四處,當她有個落腳地,追債的人就尾隨而至,致使她完全想脫離以往的一切,尋找彰子那樣無法回到故鄉,孤苦伶仃的女性,殺害她們以換得一個新的身分,從而開始一段不同的人生。
宮部的小說帶著相當濃厚的鄉愁(nostalgia)的感覺,從她的歷史小說或是偵探小說當中都可以看到,《平成徒步日記》是一本走訪日本歷史古蹟和佚史的散文,宮部以舒緩的筆調寫下她的旅程,在幾篇文章之中,他都表現出一種態度,日本歷史上最美好的日子就是那些隔絕於世,不與人來往的日子,雞犬相聞,穩定且平靜的社會。故現代這種高度流動且疏離的社會,對她來說就是傳統生活的一種崩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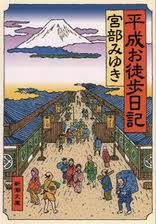
2012年4月5日 星期四
L'Étoile, Jura

在《神之雫》當中,這套除了日本以外,紅遍東亞國家的紅酒漫畫,甚至我在巴黎大大小小的酒窖之中,也看到這套漫畫的法文翻譯本,漫畫的主題是主角尋找父親所留下的十二門徒(十二支珍稀的紅酒),除此之外,也在尋找的過程之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在其中有一則小故事和台灣有關,兩位華僑的陳年紹興不小心遭到服務生打破,為了尋找能夠替代紹興酒的葡萄酒,在尋找與宴客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楊老闆「楊董」就是前駐法代表楊子葆。
能夠替代紹興酒的葡萄酒是甚麼呢?依據《時報周刊》的報導,兩年前漫畫的作者亞樹直姊弟來台,尋找一種可以搭配魚翅的葡萄酒,楊指出:「魚翅熱燙時會使味蕾防衛、收縮,白葡萄酒因而失色;配紅酒的話,又要衝突出紅酒鐵鏽味;此外,用魚翅時有時加紅醋,而醋是葡萄酒天敵。」在尋找葡萄酒的過程找到Jura,這個在法國東邊接近瑞士與德國的一個小產區。

幾年以來,相較於紅酒,我發現在飲用習慣上較常喝白酒,我喜愛的白酒一般都是法國的酒,包括:夏布利、勃根地、Bordeaux blanc、 Alsace Rieslings、Blanc de Blanc Champagne、Sancerre、Pouilly-Fume等。除此之外,我也會經常增加一下新的白酒到我的酒單之中,就像在未知的世界探索,當認識與熟悉一些之後,繼續往下深究,期待有新的刺激與味覺體驗。Jura就是一種新的刺激,她的味覺一喝就令人難忘,也難以令人輕易接受,味道強烈的白酒、知名的黃葡萄酒(vin Jaune)與濃甜的麥稈酒(vin de paille)是這一個區域的特產。
相較於其他的葡萄酒產區,Jura 的栽種面積並不大,在五十英里長和將近四英里寬的範圍裡,處於侏儸山脈之中,在其西邊有相當知名的勃根地金丘(Burgundy’s Côte d’Or)產區。Jura之下,有四個AOC產區管制的葡萄酒:侏羅山丘(Côtes du Jura)、夏龍城堡(Château-Chalon)、星星(l’Étoile)和亞布瓦(Arbois)。

最近在家中附近的SAQ買了幾罐Jura的酒,法定產區l’etoile 因為其土壤當中具有細小的星形化石而得名。味道特殊,帶著強烈的堅果香氣,很容易與其他地區的白酒分開。生產這種特殊酒款的土壤就在法國邊區嚴峻的山丘土地上,雖然它的石灰岩特性與勃根地相同,然而較為陡峭的山地,使得葡萄的栽種與生長較為困難,或許味道的強烈與特殊也由此而來。

2012年4月2日 星期一
《告白》與《贖罪》及其影像化

日本的推理女性作家從戰後以來一代一代的傳承,宛如接力棒的傳續,也有如漣漪般的散開,從職業傳承的角度而言,代代皆有新人輩出,從五○年代的仁木悅子開始,七○、八○年的夏樹靜子,九○年代的宮部美幸、高村薰和桐野夏生;從取材的角度來看,則是開枝散葉,推理小說的不同類型皆有人嘗試,而且在類型之中變化,使得推理或是說懸疑小說的活力始終不墬。
女性的推理小說,在性別與偵探小說這種類型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從推理小說肇始以來,偵探始終是男性的角色,暴力與血腥似乎是男人的場域,女人在推理小說之中總是配角、花瓶或是受害者,不然最多就是蛇蠍美人,她們能引起別人的犯罪而不自己主動動手。推理這種智性的遊戲,在沙文主義下,當然只能屬於男人。女人在推理小說之中當起主角,不管是身為警察、私家偵探或是制裁者,在血腥、暴力的危險環境之中工作,對於男性來說,基本上就是一種挑釁。如同Maureen Reddy所言,女性的推理或是偵探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工具或是手段以批評推理小說這種男性沙文主義至上的文類。
然而,或許我們可以追問一個問題,當女性在推理小說之中的角色翻轉,女性作家們或是她們筆下的偵探/解謎者/制裁者(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能夠提供給這種小說類型甚麼樣的刺激與活力?女性的角度不只是模仿男性的權力關係,必須要有一套不同的態度與角度,女性不是那些在街上晃蕩、出入酒吧的單身男性,冷硬派的男性偵探孓然一身,女性的偵探或是解謎者有她們的交友網絡、情感聯繫,不同於男性的關係。

湊佳苗(湊かなえ)在近來日本的女性推理/懸疑小說的寫手之中,無疑是展現女性角度與書寫代表性的一位,從2007年的《告白》和2009年的《贖罪》,寫作形式與結構基本相似,小說中的每一章都是由事件的不同參與者的第一人稱,以主觀的回憶述說事件的過程、細節與心理傷痕。這兩部也分別的影像化,登上電視與大螢幕,《告白》於2010年由曾經拍攝《令人討厭的松子一生》(嫌われ松子の一生)的導演中島哲也執導,松隆子主演;《贖罪》則在2012搬上電視劇,由風格驚悚詭異的導演黑澤清執導,小泉今日子、蒼井優等有名的女優主演。
《告白》的情節是中學女老師在任職的校園游泳池內發現自己的四歲女兒的屍體,剛開始以為是意外溺斃,但後來在她的調查下,原來是班上兩位學生所殺害,但他們的殺人動機不是為錢、為情或是為仇,只是為了荒謬的理由。痛失愛女的老師辭職,不向警方尋求幫助,瞭解真相成為她復仇的動力,青少年犯罪在法律上也只是輕判,無法使犯罪的少年一輩子瞭解其所犯下的罪孽,並且真心的贖罪。在結業式那天喪女的老師向全班學生告白真相,且透露了她的復仇計畫,在犯罪的學生身上埋下了恐懼的種子,讓它在心底發酵,成為制裁與復仇的計畫。

中島哲也所拍攝的《告白》,和其之前所拍攝《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的風格有點類似,指的是其帶著詩意的影像敘事,電影中還穿插著歌舞,宛如是一部一部的音樂MV所串連起來的電影,詩意帶著點歡樂的影像,背後卻是暗藏著深淵般的黑暗,更增加了反差與諷刺的強度。對於中島哲也來說,他對於這部小說感興趣的地方在於:「究竟怎樣才可以將一部用獨白講故事的小說化成影像」。由此激起改編的興趣,「就好像我們用手機通話很輕鬆平常,但要你把談話內容用圖畫去表達就很難了。」
在《贖罪》之中,則是描述五個小女孩,在學校游泳池附近結伴玩耍,一個男子靠近說因為修理器具所需,搆不到游泳池休息室頂上的蓋子,要求玩耍的某位小女孩隨同幫忙,然而,直到夕陽西下都還沒回來。雖然同學都目睹兇手帶走小女孩,但是卻都無法確切的記得他的面孔,使得案情在十幾年之間都沒有突破,受害者的母親也責怪這四個小女孩,如果她們一起隨同,慘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了,帶著愧疚的心情和受害者母親的指責,成為她們四個小孩成長的陰影,在命案追訴期即將截止之際,四個長大成人的女孩在心中的陰影之下,雖然走向不同的人生,卻都成了殺人兇手。

黑澤清的電影從《救贖》、《蛇道》、《X物語》到《人間合格》,對於人心底的黑暗與陰影掌握的十分成功,電影總是充滿了陰暗的色調、異於常規的敘事節奏與另人焦慮的氛圍,黑澤清認為:「我想描寫在人世間所遭遇到的恐怖,而這群面對死亡的人可不容易說明自己所遭遇到的可怕到底是在那裡?於是我大膽的把這兩者做一個結合,希望觀眾在看我的作品時可以感覺到那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氣氛,及人心中邪惡黑暗面的可怕。」由黑澤清指導《贖罪》,每個小孩都在從小遭遇到接近死亡的陰影,由於背負如此的負擔,使她們的人生充滿了沉重,面對世界時總是無法坦然,所見到的世界與正常長大的小孩也不同,黑澤清獨具特色的影像風格恰好與強調主觀敘事的湊佳苗的小說貼近,將每個主角心中的世界予以具像化,故在黑澤清的《贖罪》之中的影像,世界不是正常的世界,它沒有正常的色彩,人物缺乏正常的舉止,呈現出敘事者的視角與世界。
中島哲也與黑澤清這兩個導演,面對一個女性作家或是女性故事為核心的小說,他們的呈現方式就是脫離現實的色彩、線性邏輯與敘事方式,將人物心中的世界呈現出來。

回到女性作家的敘事觀點,湊佳苗小說當中的主角是女性,她們的情感世界、社會網絡或是心情的起伏是小說精彩所在,不是本格派那種重視推理邏輯的鋪陳,畢竟即使找到兇手,情感依然無法回復,事件所發生的創傷仍然背負在受害者、家人與朋友的身上;她也不單純是社會案件的呈現,戰後社會派大師松本清張的角色通常是為了脫離過去的窮困與潦倒,改變自己的身分、人生與認同而活下去。然而,湊佳苗似乎不太在乎這些,在女性的敘事中,外在的大社會固然重要,但不會比上週圍的情感來得重要,與親人、朋友和情人之間的網絡與關係,似乎才是構成她們世界的核心,故在小說的敘事上偏向主觀,她們之間的小團體就構成了一個小世界,不管外在世界如何變化,這個小世界才是她們人生所依賴、所相信的核心。
訂閱:
文章 (Atom)




